隐私与生命
纽约时报采访WHO赴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让微博、腾讯和微信向所有用户提供准确的信息。你们本可以让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也这么做。
记者:这一切在美国难道不都是不可能的吗?
你看,记者们总是说:"我们的国家可不能这样做。"人们的思维定势必须向快速反应思维转变。你打算举手投降吗?这里面存在真正的道德危险,体现的是你的易感人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说是这么说,但所有人都知道美国不可能让FANG的任何一家这样做。
西方媒体更全面的看待隔离
上文中采访了WHO组长的是NYT科学记者Donald G. McneilJr。早先他也发表了一篇评论:“中世纪铁拳是对抗病毒的答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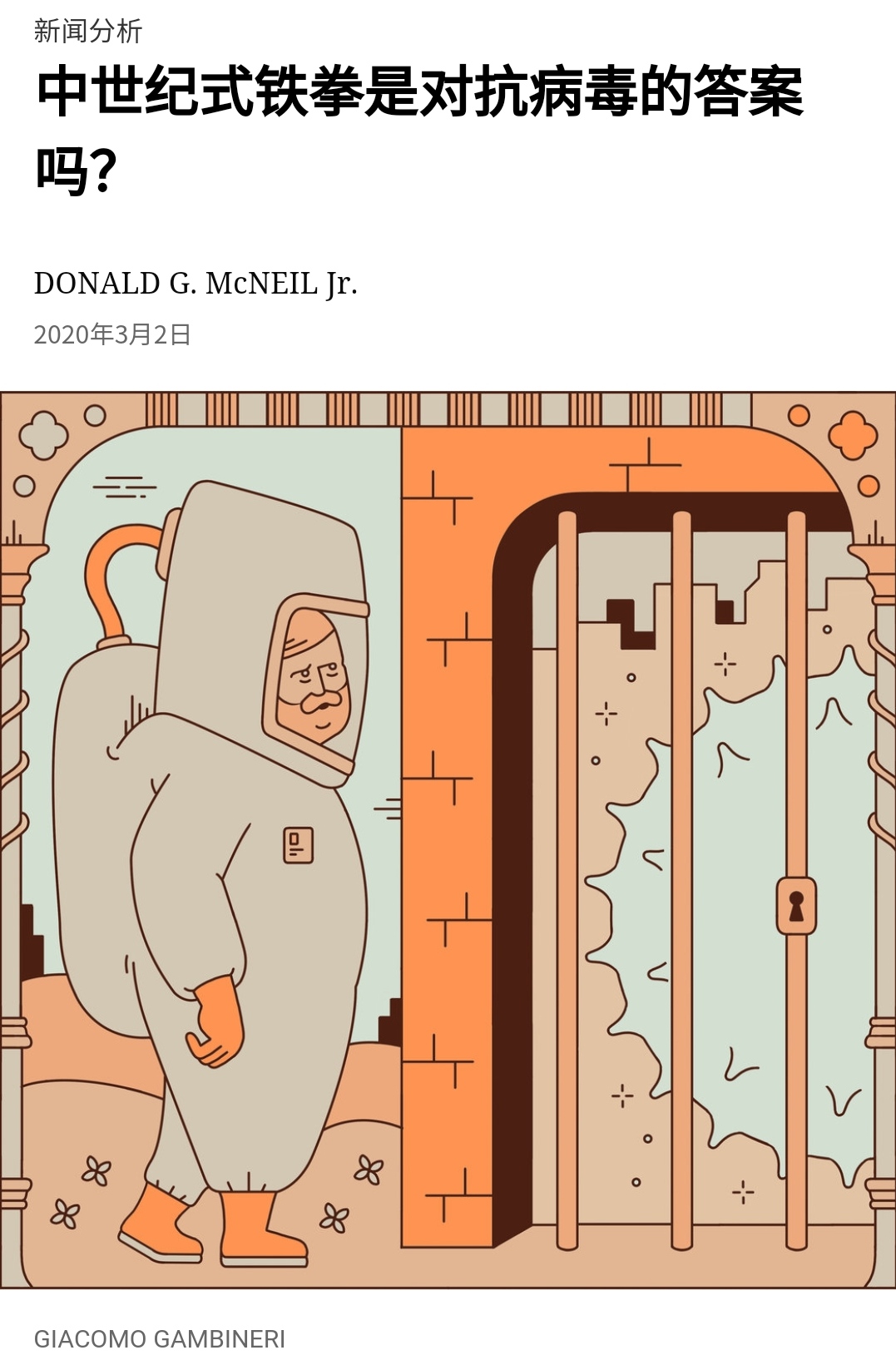
在这篇观点中你能看到NYT上一以贯之的视角,“中世纪”和“现代”的描述已经充分展现了这一点。
但这名科学记者也许是少数能正视事实的人:从科学的角度说,它确实更有效。
他举的例子还包括著名的古巴艾滋疫情:
1980年代,古巴和美国都遭到艾滋疫情的严重冲击。在古巴,病毒首先感染了曾在非洲服役的数千名士兵、医生和护士。
卡斯特罗政府的回应(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全面谴责)是强制HIV检测、把每个感染者送入隔离营。隔离营并不是人间炼狱:里面有小屋、花园、剧团演出、医护服务,还有通常比营外的人更充足的食物,更少针对男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恐惧——相比他们在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古巴农村地区所面对的。但没人可以离开,除了短暂的回家探亲。探亲还必须有一位陪同,以确保期间杜绝性行为。
与此同时,美国采取了一种支持合法权益的做法。当时,即使是提供HIV检测,若是在没有单独的专家咨询环节的情况下也是违法的,这种做法吓跑了很多需要检测的人。尽管同志浴室是传播中心,但对于关闭浴室一直存在争执。
到1990年代三联疗法创建以后,古巴的大部分隔离营已经关闭。
但选择残酷或自由,在拯救生命方面呈现出赤裸的差异:古巴的HIV感染率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六分之一。纽约市和古巴全国的人口大致相当。在艾滋流行的前30年,古巴仅有不到2500人死于艾滋。而在此期间,有7.8万名纽约人(大多是男同性恋)死于艾滋病。
由文化和制度造就的
人们没法为成年人指出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此处也无意白费口舌。
但我想说的是,何以不同。
一些显而易见的包括,过去若干年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但西方主权国家建立之前,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如此。而美国众所周知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人们能看到在面对可能需要采取隔离这样措施的公共卫生事件或者自然灾害中,美国各地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一致的。正如托克维尔近两百年前观察的那样,美国的基础建立于地方自治之上。
但更深层次的,是对一些更基本的东西的判断,比如神、理性、自由、生命等等,这构筑了不同民族的底色。
比如为什么即使面对“你的易感人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很多国家也难以做出隔离、利用隐私数据这样的举动。因为并没有一条原则说,生命比另外一些基本权利更重要。
虽然国内几乎人人都听过并颂扬裴多菲那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彼之自由与我们想象的自由之区别。
自由的概念若只是体现在革命或者存亡关头,它显然不是一个文化中最重要的事情——文化中最重要的准则已经融入了日常之中。
这也正如若干年前江访美时在记者会上自由发挥的那样,关于人类的一些共同准则我们无疑也是遵守的,但对于一些具体概念的理解,则受到距离、文化、发展程度等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人们看到的巨大差异,不在于对字面意义的理解,而在于活的应用,体现在现实秩序当中的优先级。
当然,我们今天的环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并非是文化能全部解释的。
中国文化中是否有“集体主义”精神?
我理解恐怕是没有。首先集体主义是最近一百年的舶来品。在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在农村公社之后,它也迅速破产了。
集体主义并不像字面理解的那么回事,它更像奴隶制或者军国主义的残余,强调的是秩序和服从。
有人说不正是这样吗?至少在当下,这是一种混淆。
中国自古以来呈现的是秩序和失控的交替,是法家严苛的控制与流民暴动的交替,很难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中看出一丝一毫的”集体主义“来。
人们看到四面八方支援湖北、武汉,看到各种灾难之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其实是两个事实,一部分来自中央集权和威权政治,因为绝大部分快速动员是国家机器来完成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人们再感动在行动上也实现不了这一点。
但另一层面,附着在国家机器动员之上,人们对此的认同确实是一致的;国家机器之外的零散民间自发行动也能体现出这一点。
而疫中的武汉人呢?WHO到访武汉,其中一名专家后来在日内瓦记者发布会上说,她最大的触动就是**“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
如果从我们的文化中寻找根源,前者曰仁,后者曰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无非是人类从人类最基本的恻隐之心等基本的情感中进一步阐发,根源是普世的,但仁义变成了我们独特的文化内核。
最近网上也多传许知远采访许倬云的一段视频,其中90多岁的许倬云谈及抗战的牺牲、四川农民同赴国难(抽丁两百万)时涕泗横流。

如今人们对此的感受,可能多半就如读史读到崖山,难以置信南宋十万军民蹈海一样。此仁义传承于国难时,而今仁义显于微时。
媒体之中,惟《财新》对此展示最为贴切,他们报道医护人员牺牲的文章,专题叫**“仁心赴国难”**。
这是我们的内核,因为我们会真正的运用它们。
